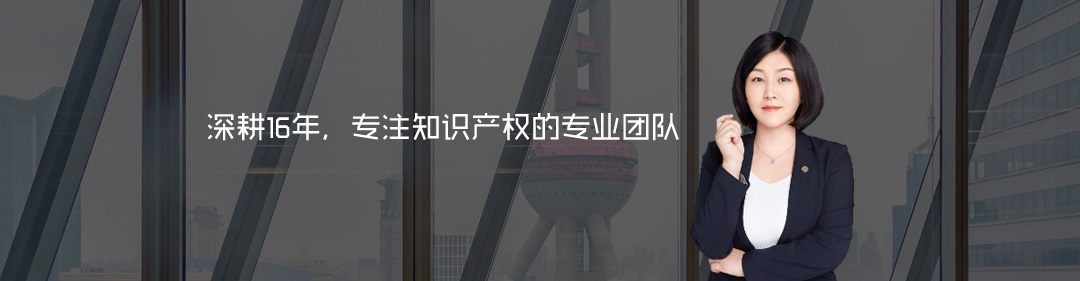【内容提要】制造他人商标标识的行为人未尽到查验委托人证明材料义务的,构成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商标标识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廉,擅自制作他人商标标识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不能依照标识制造商的侵权获利计算。
【案情】
原告:上海霍山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帝求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凯顺京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南大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协心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第三人:上海霍山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地球牌”文字加图案商标(涉案商标)系上海交通电器制造厂于1951年10月16日注册取得。注册号为第10315号,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9类,用于汽车上的点火线圈、电器开关、保险器、保险丝盒,接线板、插销插座。后经多次转让,该商标于1991年3月30日由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受让,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03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
2004年11月1日,上海汽车电器总厂与第一原告上海霍山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商标使用协议,内容是:上海汽车电器总厂进入消壳,为更好地为转制企业服务,订立本协议。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同意第一原告生产的汽车电器产品无偿使用“地球牌”等商标。第一原告在使用商标前,必须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商标被许可使用手续,许可使用期限为自2004年11月起至上海汽车电器总厂消壳之日。由于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处在阶段性消壳的特殊阶段,如果正式消壳,商标将有偿转让给第一原告,转让费为人民币8000元。2009年2月13日,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出具一份授权书,内容是:作为“地球牌”商标的所有人,上海汽车电器总厂授权自己的改制企业第一原告、第二原告作为“地球牌”商标使用人,可以对国内任何侵犯该商标权利的人行使包括诉讼在内的任何保护和索赔权利。2009年4月,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第二原告是上海汽车电器总厂经营部转制后的企业,享有“地球牌”商标使用权。
涉案商标被使用在第一原告生产的汽车点火线装置外包装上的防伪标签上,该标签上有“地球牌”文字加图形商标、上海汽车电器总厂以及第一原告的名称、防伪码、免费电话和热线电话内容。第三人上海霍山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是第一原告的全资子公司。2007年3月,第一被告北京凯顺京达科技有限公司接受第三人员工吴若愚的委托,先后制作了涉案防伪标签15万枚,每枚0.025元,共3750元,而吴若愚提供的商标权委托材料为复印件。在制作过程中,第一被告委托第二被告江苏南大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防伪技术服务的平台,提供电话声讯查询服务,约定每枚0.005元,第二被告明知第一被告入网企业资质不全。2008年11月,第一原告在市场上发现涉案的假冒防伪标签,除查询电话与第一原告的真实标签不同外,其余内容都一致。2008年11月20日,第一原告向第三被告上海协心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购买了贴有涉案假冒防伪标签的假冒点火线装置。
原告诉称,上海汽车电器总厂曾是隶属于上海汽车集团公司的大型国有企业,其拥有的地球牌商标汽车电器曾是中国第一汽配品牌,驰名中外。然而由于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产品,使该厂无法冲出重围,最后从年产值几亿元、员工近5000人的企业沦落改制为百余人的两原告。“地球牌”商标也由原告使用。近来,假冒商标产品上出现了防伪查询电话。这次,原告经过长期追踪调查,终于查获了第一被告制造销售“地球牌”商标标识15万枚、第二被告提供查询平台的事实。第三被告仅仅是原告随意选择的无数个销售粘贴该假冒“地球牌”标识汽配件的销售商之一。被告的商标侵权行为给商标持有人和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原告向第三被告购买的价格是45元、原告委托生产收购价为19元,毛利26元,15万个则为390万元。律师费4万元、调查费4万元以及公证费2000元。原告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商标法的法定赔偿原则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严厉打击已严重泛滥的假冒伪劣违法行为:一、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二、判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共同赔偿两原告人民币各40万元,包括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判令第三被告赔偿两原告人民币各295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被告北京凯顺京达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一原告与上海汽车电器总厂签订的商标许可协议是普通许可,其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无权自行起诉。第二原告与上海汽车电器总厂未签订任何许可协议,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第一被告为第三人上海霍山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制作15万枚防伪标识有合法授权。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江苏南大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辩称,第二被告不构成商标侵权。第二被告没有直接印刷商标,而是接受第一被告的委托提供防伪技术服务的平台,即按照第一被告的要求录制录音,按数量分配码段并提供防伪码的声讯服务系统查询。第二被告在提供防伪技术服务的过程中,审查了第一被告提供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第一原告的委托书、第三人的指定(委托)书等文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
被告上海协心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辩称,2008年9月,有人上门向第三被告推销地球牌商标标识,第三被告就花1万元买了1000张商标标识,将标识贴在第三被告从其他厂家进的散装高压线上进行销售。散装的高压线外包装上已有商标和生产厂家,进价约17-19元,不贴含有涉案商标的防伪标识的商品销售价约23元,贴后售价为40元左右。第三被告销售了约480个,接到法院的诉状后知道不能用了,就把剩余的标识全部销毁了。
第三人上海霍山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述称,第三人是第一原告投资的子公司。第三人与上海汽车电器总厂没有涉案商标许可使用关系。第三人没有委托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制作涉案商标。第一被告出示的盖有第三人公章的指定(委托)书是假的,不是第三人的公章。两原告也没有委托和许可第三人使用、制作含有涉案商标的防伪标识。
【审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原告作为涉案注册商标的普通许可使用人,经过商标权人的授权,有权提起诉讼,追究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第二原告经过商标权人的授权,有权提起诉讼,但因没有实际使用涉案商标,无权获得损害赔偿。依据《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均负有查验委托人证明材料的义务,而委托人持有的商标注册人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商标使用人第一原告的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故第一被告没有尽到查验义务。第二被告在第一被告证明材料存在问题、入网资质不全的情况下仍然交付防伪码、提供录音和电话声讯查询也存在过错。故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构成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共同侵权、第三被告购买了假冒的商标标识贴在假冒产品上并销售的行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侵权行为。关于赔偿数额,两被告制作防伪标识获得的收益不会超过人民币3750元,但是,本案尚存在其他侵权人,其他侵权人的获利无法查清,且有多少侵权标识流入市场也无法查清,故不能以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的获利来决定本案的赔偿数额,也不能以第一原告所称每个假冒防伪标识会造成26元的利润损失来计算赔偿数额,法院综合考虑涉案商标的价值、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的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损害赔偿额。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16条、第17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一、三被告停止对第10315号“地球牌”文字加图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二、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第一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和合理开支人民币2000元;三、第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第一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万元;四、驳回第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评析】
一、两原告是否享有诉权?能否获得损害赔偿额?
依据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商标侵权纠纷案件,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侵权人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包括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在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时,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商标注册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本案两原告作为普通商标使用许可人,经过商标注册人的明确授权,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权。
但普通商标使用许可人能否获得损害赔偿额却与被许可商标是否实际使用密切相关。依据损害赔偿额确定的填平原则,只有存在实际损失,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商标的实际使用是损失产生的前提,实际使用使商标被许可人获得获取经济利益的市场,他人的侵权行为致使被许可人市场份额减少,从而给被许可人造成损失。而商标没有被实际使用,被许可人不会产生损失,也就无法获取损害赔偿额。
本案涉案产品显示第一原告和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在共同使用该商标,而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已经进入企业改制后的消壳状态,并不实际从事经营活动,涉案商标的实际使用人为第一原告,故第一原告享有请求损害赔偿额的权利。第二原告没有提供其与上海汽车电器总厂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且涉案产品也没有涉及第二原告,其无法证明在本案侵权发生时其生产、销售带有涉案商标的产品,故第二原告非商标的实际使用人,没有损害产生,不能获得损害赔偿额。
二、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
依据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第一被告实施了制造涉案侵权标识的行为,第二被告实施了为涉案侵权标识提供查询平台的行为,两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在于双方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即是否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
根据《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防伪技术产品生产企业在承接防伪技术产品生产任务时,必须查验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包括:(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有关身份证明材料;(二)使用防伪技术产品的产品名称、型号以及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质量检验机构对该产品的检验合格报告;(三)印制带有防伪标识的商标、质量标志的,应当出具商标持有证明与质量标志认定证明。第一被告受第三人委托制作带有涉案商标的防伪标签,由于没有相应资质,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订购防伪码和声讯查询服务,又委托他人印刷标签,故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均应该查验委托人的有关证明材料。
现第一被告持有的证明材料除盖有第三人公章的指定(委托)书为原件外,商标注册人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商标使用人第一原告的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经鉴定。指定(委托)书上的公章印并非第三人公章所盖,第三人也否认其出具过该份指定(委托)书。即便如第一被告所称其基于吴若愚身份而相信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但是第二被告发回的入网企业资质不全的回函传真十分明确指出第一被告提供的证明材料存在问题,因此第一被告在查验委托人的有关证明材料时存在明显的过错。第二被告在明知入网企业资质不全的情况下仍然交付防伪码、提供录音和电话声讯查询,也存在过错。第二被告称其没有印刷商标标识,但是其从第一被告提供的材料中明知防伪标签涉及商标,如第二被告不提供防伪码和电话声讯查询,第一被告也无法印刷有防伪码和电话查询的防伪标识。因此,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第一被告对第二被告作出的一切后果由第一被告自己承担的承诺,是合同行为,具有相对性,只能约束合同相对方,对原告没有效力,因此,第二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三、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损害赔偿额的确定。
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赔偿数额的确定有三种计算方式,但无论哪种计算方法,计算结果都应该是相当的,因其都是对权利人损失的填平。但本案两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与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却相差甚远,两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不会超过3750元,但权利人因侵权造成的损失却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假设15万个注册商标标识均被贴在假冒商品上进行了销售,则原告的实际损失近40万元。
造成两种计算结果严重不相当的根本原因是权利与权利载体价值的不对等。商标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起到的是区分产品来源的作用,侵犯商标权会抢夺权利人市场,从而给权利人带来经济损失。而承载商标标识的载体作为一种有形物,其价值是确定的,就是纸质与印刷的价值。本案侵权人的获利计算是针对权利载体的,不可能与本案原告就商标权受到损害而主张的损害赔偿额相当。因此。不能适用被告的获利来确定本案的损害赔偿额。
商标侵权中权利人获得的损害赔偿额是对其因他人侵犯其商标专用权所遭受损失的一种填补,即适用的是填平损失原则,因此,损害赔偿额的认定应当以权利人的损失认定为基础。这就需要区分商标侵权行为的两种类型。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情形的商标侵权行为,其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直接侵权行为,即核心的或者基本的商标侵权行为,其直接妨碍了注册商标发挥其商标标识功能;另一种是外围的商标侵权行为,其虽然不直接妨碍商标功能的发挥,但为直接商标侵权行为推波助澜或者为虎作伥,如扩散侵权后果、为侵权创造条件。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行为就属于外围的商标侵权行为。两种侵权行为导致的商标权利人的损失不同,直接侵权行为直接产生了权利人的损失,两者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外围的商标侵权行为则不同,其并不直接导致权利人损失的产生,如本案中若15万个含有涉案商标的防伪标识没有被贴在假冒产品上销售,则不会对权利人产生损失。本案权利人的损失产生的过程如下:制造假冒商标标识——销售假冒标识——购买假冒标识并贴在假冒产品上——销售该假冒产品——权利人市场减少,故在制造假冒商标标识后的有关涉案假冒商标的流转都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原告的损失实际上是无法确定的,被告的侵权行为只是原告损失产生的一个作用力,因此,不能适用原告所称的一个标识造成其26元损失的方法来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法定赔偿的方法。在确定赔偿额时,既要考虑擅自制造注册商标行为对权利人损失起到的作用,也要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就两被告的侵权行为而言,虽然其并不是导致原告损失的全部作用力,但这些侵权标识为防伪标识,其在市场上迷惑性较大,行为后果较为严重。就两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而言,两者虽未尽到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查义务,但其主观是过失而非故意,本案中委托第一被告制造假冒标识的吴若愚系原告全资于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其身份致使第一被告较易采信有关涉案商标证明材料复制件的真实性。且吴若愚提供的证明材料非常具体,只有熟悉第一原告和上海汽车电器总厂的内部人员才可能制作或得到,故第一原告或涉案商标的注册人上海汽车电器总厂也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因此综合考虑涉案商标权的价值、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与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0万元人民币。
本文首发于《人民司法》2011年第12期,作者:孙黎,郭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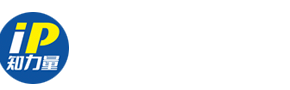 IP知力量 郭杰知识产权团队
IP知力量 郭杰知识产权团队